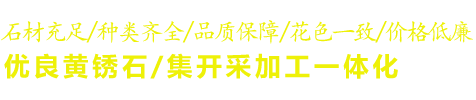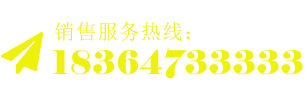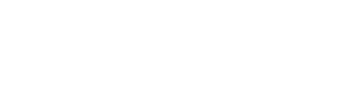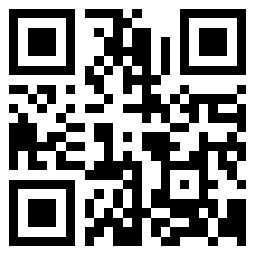详细说明/DETAILED DESCRIPTION
1937年8月25日,刚刚成立的新军委立即发布了《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随着命令的发布,129师诞生了。
他们中的部分人刚刚从河西走廊返回,还带着伤痛和疲惫,但伤痛没能使他们消沉,他们抖擞起精神,又坚定地走上了抗日战场,并在抗日战争中屡建战功,使日军闻风丧胆。
我们不仅应该认识这支部队,而且还应该牢牢记住这支后来被称为刘邓大军的部队。
不过,在115师、120师开赴抗日前线后,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内,129师按兵不动,迟迟没有出发。
这个举动,决不是有意保存实力,而是为了在国共谈判中争取到更加完整的抗日权利,采取的一个充满艺术性的战略步骤。
1937年7月14日,“七七”事变后一个星期,军委发布命令,要求红军以10日为限,以军为单位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编制,同时搞好出征前的军政训练。
7月22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在陕西三原县云阳镇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讨论红军改编以及开赴抗日前线日,在敌持续不断的增加兵力,华北战局危急的情况下,八路军不待改编完毕,即以115师主力由陕西省三原地区誓师出征。
从上面的时间表能够准确的看出,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爆发后,领导下的八路军为了配合友军作战,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心情是多么迫切。
八路军没有等待,“不待改编完毕”,就将两个师的主力开上了前线师没有动。军委在等待着国共两党的谈判结果。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初步实现了国内的和平,初步形成了国共两党的合作。
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实现全国抗战,自1937年2月开始同当局举行了多次谈判,但双方条件差距太大,谈判陷入僵局。
方面,蒋介石强令红军师以上干部全部出洋,一年后再回来量才任用,4.5万红军改编为3个师3.3万人,不设总指挥部,分派到各战区作战。
而我党坚持对红军的领导地位,坚持红军改编后设总指挥部,各级指挥官人选由我党来定,同时要求蒋介石公开发表承认合法地位的宣言。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日军进攻上海,威逼南京,蒋介石在华东的统治受到直接威胁,当局才被迫和达成协议。
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同意设总指挥部,下辖3个师,每师1.5万人。
随后8月25日,红军即发布了改编令。8月31日115师东渡黄河。9月3日,120师也挥师北上。
早在7月15日,周恩来在庐山上亲自将的《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了正在休假的蒋介石。
8月中旬,蒋介石在南京同中国的代表周恩来等举行了1937年2月以来的第5次谈判。
谈判中,蒋介石企图把宣言中的政治主张删掉,只将红军服从国民政府军委会指挥的字样加以宣布,以造成完全臣服于的假象。
同时,蒋介石还要求任命复兴社头子康泽为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一百多名复兴社特务分子担任八路军各级政工人员。
和周恩来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是很坚决的。7月28日,和周恩来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指出:3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以便指挥作战,不要康泽。
就如同下围棋一样,蒋介石想在抗日的问题上抢个先手,而让落个后手,但很少下围棋的,却深谙棋理,招招不让。
根据中央的指示,谈判小组明确向蒋介石表示:129师出动的条件,即由当局发表《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承认中国的合法地位。
9月下旬,蒋介石同代表举行第6次谈判,迫于各方面的压力,蒋介石不得不于22日授意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第2天,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的合法地位,历时半年多的马拉松式谈判终于徐徐降下帷幕。9月30日,八路军129师由庄里镇出发,向晋北急进。
由于蒋介石给的编制少,红军一个军只能改编成一个旅,一个师只能改编成一个团。因此,红军改编后装备虽不精良,人员却很充足。
八路军一个旅下辖两个团,每团下辖3个营,每营下辖4个连(3个步兵连,1个机枪连)。这是蒋介石定了的,无法突破。但每个单位的人员都是按最高配额配备的。
比如由原红4军10师改编而成的769团共有2900多人,基本上和红军时期的一个师的编制差不多。
129师出发后,日夜兼程,向着晋北急进,上上下下只有一个想法:尽快赶到前线,尽快投入到对日军的作战中。
忻口会战前夕,中央军卫立煌和汤恩伯两个纵队进入山西,阻挡南下的日军坂垣师团。
八路军总部曾经有过以八路军主力在日军侧翼主动出击,配合军正面防御的设想。因此让129师主力兼程北上忻口。
可由于日军在平汉路方向推进得异常迅速,并转兵经正太路迂回太原,于是具有正太路咽喉之称的井陉、娘子关段,就成为了双方争夺的重点。
为配合友军遏制住日军在这一方向上的进攻势头,129师386旅在到达太原后,没有继续北进,而是转向东,奔向正太路东段。
由于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实行封建割据,长期闭关自守,同蒲铁路和正太铁路修筑的都是窄轨铁路,铁路运输效率低,车行速度慢。
从太原到平定只有700多里路程,却要走近25个小时,平均时速不到15公里。
陈赓率772团到达平定后,由于军队“纪律甚坏,到处抢劫,十室九空。”所以当地群众十分害怕,纷纷“奔避”。
“经我们解释后,明白我们为红军,对我们特别表示好感,不到一时,逃避群众陆续回家。”
129师386旅到平定打的第一仗恰恰是为解救让陈赓感到愤怒,使“群众奔避”的第3军曾万钟部。
由于国共两军在晋北前线的顽强战斗,日军坂垣师团前进缓慢,伤亡惨重,与忻口一线的中方守军形成对峙。
从河北撤出的军一部、孙连仲的第2集团军、冯钦哉的第14军团、曾万钟的第3军,以卫立煌为前线总指挥转用于防守娘子关一线日,也经同蒲路转正太路赶到了驻在平定的386旅旅部。
此时,由正太路西进的日军第20、109师团已占领娘子关东南的旧关,正在向娘子关猛攻。
由娘子关南侧实施攻击的日军第109师团主力经九龙关、测鱼镇等处,沿正太路南侧山地西犯,企图对娘子关正面的守军实行迂回攻击。
娘子关一线的军防线已被撕破,部分军已向后撤退,第3军一部和武士敏第169师则被围困在旧关以南的山地,晋东的形势十分危急。
10月20日,陈赓率领772团到达了娘子关以东的长生口附近的支沙口。陈赓遵照的指示,命772团一部袭击板桥西北高地的日军,以解军被围之急。
执行袭击任务的是772团3营。3营的前身是红四方面军的279团,以长于追击歼敌而闻名,是有名的“飞毛腿营”。
21日夜,3营在副团长王近山的带领下,向板桥出发了。王近山是被人称作“王疯子”的虎将,改编前任红31军93师师长。
3营刚过长生口,便遇到了新情况,前面板桥方向来了一队日军,正偷偷向西进犯。
此时向上级请示已经来不及了。一向果断、坚决的王近山立即命令部队利用两侧山地的有利地形,作好战斗准备。
一个包围圈,一个埋葬日军的坟墓迅速地形成了。100多名日军毫无知觉地进入了包围圈。
当日军一个不剩地全部进入包围圈后,随着王近山一声“打”,3营所有的轻重火器同时开了火,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了一片。
在八路军的猛烈打击下,日军只有招架之功而毫无还手之力。经过一个小时的战斗,当曙光初露时,大部日军被歼,只有一小部日军被压缩在长生口村的一个空场院里。
这是386旅抗战的第一仗。兄弟师115师首战取得了平型关大捷,兄弟旅385旅的769团初战也取得了奇袭阳明堡的胜利.
所以,当战士们向龟缩在场院里的敌人最后冲锋时,一个后来成为我军高级军事领导人的前线指挥员突然喊了一声:“捉活的!”
这个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常常会出现的战斗环节,往往标志着胜利的最终到来,也往往将一场战斗的胜利推向高潮。
当仍然遵循着和作战老套路的八路军向残敌发起冲锋时,大喊“缴枪不杀”,遭到日军负隅顽抗,有11位勇士倒在了残敌的枪口下,残敌也乘机逃脱了包围圈。
长生口战斗共毙敌50余人,缴枪30多支及一些弹药等军用品,这一仗八路军以一个营的非常大的优势兵力,却没能消灭100名日军,是一个巨大遗憾。
不过,这并不辉煌的胜利,却是386旅的抗战第一仗。虽然胜利中有教训,但它仍大大地鼓舞了386旅的士气,也使386旅用胜利的实践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为了进一步地了解情况,9月21日来到了在娘子关担任正面防御的军第3军军长曾万钟的指挥所。
曾万钟首先向介绍了日军新的动向。他说,近日日军第20师团避开娘子关正面阵地,集中兵力和火力正向右翼的新关猛攻。
新关守军凭借窑洞式半永久性工事和钢骨水泥永久性火力点进行防御,予日军以重大杀伤。娘子关的守军也随时准备出击支援,这样的部署,日军是难以从娘子关突破的。
对曾万钟说:“日军不攻娘子关而攻新关,是想来个避实击虚。如果新关也不易得手,它极可能再往南迂回。这样,新关以南的石门,则必须火速派兵占领,严防日军偷袭。”
和曾万钟会谈之后,形势的发展正如所料。只是曾万钟的疏忽,殃及了129师386旅771团,当然其中也有771团自身的疏忽。
10月22日,日军在新关攻击失利后,派出第40旅团5个大队进行右翼迂回,从井陉方向迅速占领了石门口。
当夜,日军依据侦察机提供的情报,避开大路,从谷底小沟绕了过去,对771团发动了突然袭击。
前一天,得知771团在利用当年蒋介石、阎锡山军阀混战时期的旧工事备战时,曾提醒他们说:“不行,旧工事不可靠。”
由于771团警戒不严,没有对日军的偷袭组织起有效的抵抗,一下子就被冲散了,团主力不得不撤到附近的山上。
形势是很严峻的,被偷袭后的10多个小时内129师师部及386旅旅部与771团完全失掉了联系。是在焦急地等待中度过了最初的几个小时。
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二级上将黄绍竑得知此事后,从太原打来电报“慰问”。
他带着嘲弄的口吻说,你们八路军光说游击战、运动战,结果你们反被日本人游击掉了。
第2军团司令兼第13军军长汤恩伯得知这个情况后,也打电话给说:“看来你们的游击战不行哪,我们几万人都顶不住,你们一个旅怎么行?还是撤吧!”
就在军的一些高级将领嘴上轻蔑的微笑还没有消失的时候,771团以自己出色的表现,以八路军所特有的顽强与机智,向他们表明:
日军在炮火掩护下,突入了771团的阵地。771团一开始确实很被动,上级与下级失去了联系,自上而下的指挥已经不复存在。
771团被冲散的每个部分自动的组成新的战斗集体,自动形成新的指挥,成排建制的就以排为单位,成班建制的就以班为单位,总之是各自为战,形成了一个个的堡垒。
并在单打独斗中,堡垒与堡垒间逐步发生了火力联系,相互掩护着向山上转移,利用山势在山上与日军形成对峙。
在已经隐约能清楚看到鬼子身影的时候,团部仅有的几个通讯员,临危不惧,又3次进入团部,将团部的公文和其他东西搬得一干二净,在鬼子眼皮底下带着文件归了队。
3连5班8名战士在坚守阵地的过程中伤亡了7名,仍然坚守阵地,不能动的给能动的准备手榴弹、压子弹,没有让一个日军进入阵地。
有的戴着缴获的日本军的黄五星帽,有的穿着日军的黄呢大衣,有的把自己的枪换成了三八式步枪,每个人手中都有一两件从日军手中缴来的战利品。
一个目睹了整一个完整的过程的新闻记者由衷地写道:他们打的胜仗倒并不叫我们怎么惊奇,他们打的败仗才真叫人佩服。
后来,见到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时,对他说了以后还说了很多次的一句话:“你培养的队伍是打不垮的!”
事后,就七亘村被袭一事给中央写了一份检讨报告。看了报告之后,于10月25日电示八路军总部和各师:
“屡胜之后,必生骄气轻视敌人,认为自身了不得。771团七亘村受袭击,是这种胜利冲昏头脑的结果。这种老子天下第一的骄气必须打掉。”
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常说:坏事可以变好事!七亘村771团被袭一事就是如此。
被袭是件坏事,但正是日军偷袭的枪声把的注意力吸引到了七亘村附近的这片险要的地形上,从而由一次被袭演化为连续三次的伏击,由一次小的损失发展为连续大的胜利。
当亲自赶到771团被袭地点察看时,他一下子就被眼前的地形给吸引住了。
从河北井径往山西平定的小路,由石门口进入峡谷,谷深几十米,最窄处只有3、4米。
小路蜿蜒至七亘村东,被断崖所阻,转而爬上山腰。山腰上的路只能在陡壁上开凿而成,更是窄小、陡峭。
迅速将七亘村的情况用电话告诉了陈赓,并指示陈赓再派人仔细侦察,选择最有利的地形布置伏击阵地。
这话有一定道理。常算一笔帐:伏击战中敌我的损失比率是多少,袭击战中敌我的损失比率是多少,阻击战中的敌我损失比率是多少。
因此,他得出一个结论:从现有的武器装备对比的情况出发,八路军进行伏击战是最合算的。
从七亘村回来后,即导演了非常精彩的“重叠的设伏”,狠狠地打击了沿正太路西进的日军第20师团。
由川岸文三郎中将师团长率领的日军第20师团,1937年7月11日在朝鲜接到开赴中国的命令,16日从朝鲜出发,19日主力抵达天津。
9月初,20师团又与第6、第14师团共同沿平汉路向南作战,至10月初,一举拿下正定、石家庄、井陉,完成了日军高层关于攻略河北西侧的任务。
日军第20师团在南下的路途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沿途军队层层抗击,使日军死伤惨重。
在平津地区作战伤亡的6000余名日军、在保定地区作战伤亡的8000余名日军名单中,有长长的一串是属于第20师团的。
但川岸文三郎并不为此感到愧疚。他懂得攻城夺地的道路是用士兵的血和肉,甚至是尸体来铺垫的。
舍不得孩子打不着狼的道理川岸文三郎是明白的。只要能打到狼,作出些牺牲在川岸文三郎看来是值得的。
川岸文三郎最不想得到的结果,在娘子关附近因领导的129师伏击而发生了。
日军为迅速突破娘子关,派出一部兵力从娘子关右翼实施迂回。25日,在日军的猛攻下,军娘子关右翼东回村南北一线被突破,国军撤回到娘子关附近的旧关。
从全局上看,军的撤退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全局劣势的情况下,仍然要争取局部的优势。
但军在全局处于被动时,在局部仍然没有争取到主动,使娘子关右翼完全暴露给了日军,在局部立时处于极端的不利,使整个防御体系面临崩溃。
日军为了加紧娘子关右翼的攻击,必然要通过井陉——平定小路向前方输送大量的后勤补给物资。抓住日军的辎重车队,打它一下子,是有把握的。
事情正如所料:25日下午,日军20师团开始向平定方向进犯,其辎重部队约1000余人,在距七亘村10公里的测鱼镇宿营。
听到这一条消息,拿着红铅笔,走到地图前,画了一个红圈圈住了“七亘村”3个字,并对师部的作战人员交待道:
将伏击任务交给了陈赓。陈赓接到命令后,决定以772团一个营的兵力到七亘村设伏。
王近山率领3营来到了七亘村的南侧山地。据侦察得知,向平定方向进犯的日军第20师团的后方辎重部队1000余人,第二天要经过七亘村向平定前进。
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王近山只有5个连,而日军有1000余人,既来不及请示,也来不及增调部队,只有靠自己手头的力量啃这块“硬骨头”。王近山没有犹豫,没有退缩。
果敢、坚决是王近山成为军中虎将的主要的因素,虽然有时这个性格特点和他很文气的外表对不起号来。
王近山将重机枪架在距道路约300米的制高点上,将部队散布在距道路10多米到四、五十米不等的长满杂草、灌木的土坎上。
王近山趁热打铁,要求部队在听到冲锋号和重机枪响后,迅速地扑下山去,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速战速决。
10月26日上午7点多,前方侦察人员送来消息,日军辎重部队300多人,在前后各100多日军掩护下,正向七亘村运动。
王近山迅速将情况通报给营、连指挥员,指示各连准备战斗。各连迅速按命令跑步进入阵地。
按预定计划,12连担任正面突击;11连担任配给轻机枪3挺,负责切断日军辎重部队同前面日军的联系;特务连一个排负责切断日军辎重部队同后面日军的联系;其余为预备队。
日军没有把军放在眼里,更没把八路军当回事,认为八路军只能隔靴搔痒,丝毫构不成威胁。
所以,当10月26日上午9时,日军辎重部队在步兵掩护下,发现没的大部队后,便大摇大摆地进入了772团3营的伏击圈。
日军第20师团由平津向南一路平推过来,除了和军打过几次阵地战外,还没有品味到中国兵学的奇深奥妙。这次伏击使川岸文三郎补上了这一课。
正当他们穿行在峡谷中,欣赏着深谷中的风景时,由各种轻重武器中发射出的弹雨倾泻到了日军的头上。
毫无遮拦,毫无退路,日军只有看着子弹把身边的人打倒,看着手榴弹在队伍中爆炸,将带着血肉的肢体抛向空中在周围飞舞。
在一阵令日军心惊胆颤的急袭过后,王近山指挥伏击的部队和预备队冲向已经晕头转向的日军。
冲在最前面的12连的一个战士,在连续刺死6个敌人后,身上除多了3处刺伤外,还多了3支三八大盖。
另外一个战士,身上多处负伤仍然不下火线,他将一个倒地的日军扑在身下,用手抓,用牙咬,在敌痛不可忍时将其击毙。
周围的民兵和群众有组织的投入了战斗,中学生组成的战地服务团也参加了进来。
一个叫董三元的老汉,战斗后用一挺缴获的机关枪从手里换来了一床军用毛毯;并被赞为“战地老英雄”。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除一部日军逃回测鱼镇外,共歼日军300多人,并缴获了300多匹骡马和大批的军用物资。
很多战士都戴着钢盔,穿着黄呢子大衣,腰间还挂着战刀,全套的日式装备,胜利的喜悦洋溢在每一个人的脸上。
战斗后,陈赓在日记中写道:今日终日搬运战利品。群众无需雇请,自动参加搬运。
第一次伏击是一次成功的、出色的伏击战,可在战后却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设想:在七亘村再来一次伏击!
从战史上看成,成功的伏击战俯拾皆是,但在同一地点连续设伏的战例却极难找到。
第一次伏击后,仔细分析了形势,认为:日军侵犯华北以来,一直是在打胜仗,七亘村的伏击,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很小的遭遇战。他们骄横得很,目空一切,并不把八路军放在眼里。
古人云:用兵之法,贵在不复。这句话中的“不复”,用现代语言讲就是不重复。
言下之意是告诫统领军队的人,在用兵时要不断想出新办法。这样的语言我们还能说出很多——“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等等。
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日军在经过遭到痛击的地点时,肯定会严加戒备,如临大敌。
在这种情况下,伏击的前提突然性已经不复存在了,若是在同一地点再次设伏,实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但只有胆大还不够。假如没有另外两个看似平淡,实际上细致入微,欺骗性很强的的行动,是很难使日军产生盲目的自信,再次在七亘村遭受伏击的。
首先,第一次伏击后的第二天,在日军来收敛被击毙的官兵的尸体时,772团一触即退,佯装败走。
这使日军产生错觉,认为八路军已无再战能力,从而以“示形于敌”之法来诱使日军作出错误的判断。
再有就是巧妙的隐蔽。28日晨,敌人的辎重部队果然循原路过来了,前后有100多骑兵、300多步兵作掩护。
吃了亏的日军再次来到七亘村后,其先头部队对道路两侧进行了严密的搜索,遇有可疑处便反复发炮轰击。
第七七二团第三营的指战员们隐蔽在灌木、草丛和石洞里,沉着镇定、不发一枪。
就在日军的眼皮底下,埋伏的八路军战士没有露出一丝痕迹,使日军更加“自信”。
11时许,日军进入了伏击地域。第七七二团第三营的机枪、步枪一齐响了起来,组成了严密的火网。
这次日军已有精神准备,一遇打击便就地组织抵抗。第三营在兵力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仍英勇出击,将日军截成两段。
由于负责增援的第二营因天雨路滑,没能按时赶到,因此第三营没能将敌全歼。战至黄昏,敌人乘夜色朦胧,突围而出,一部向西逃往平定,大部向东退回测鱼镇。
伏击在有些人眼里是很玄的一件事,设伏的前提是被伏者要在设伏者设伏的时间里通过设伏的地点,除非能像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否则设伏不就变成了赌博吗?
之所以能够把在别人眼里很玄的一件事,变成为实实在在的具体行动,是依靠他常常挂在嘴边上的“五行术”。
借用古代自然观中的“五行”一语总结了关系到敌我双方胜负因素的五个方面:任务、敌情、我情、地形和时间。
从中即可看出,的设伏,不是盲目的“赌博”,而是建立在对客观情况确实的把握上。
七亘村两次重叠的设伏,狠狠地打击了沿正太路西进的日军第20师团。但八路军的力量毕竟太有限了。
彭德怀在抗战期间曾经说过:如果八路军经常有20万,有蒋介石嫡系的装备,再附加若干炮兵,山西是难以打进的。
但当时八路军只有3个师,而不是20个师。129师两个团的力量挡不住日军西进,的数万军队也没能挡住日军沿正太路西进。
就在七亘村第一次伏击的同一天,日军攻占柏井,直接威胁娘子关与旧关守军的侧背。
在不利的态势下,军弃关西撤。日军29日占领平定,30日占领阳泉,11月2日占领寿阳。
忻口失守是华北战局恶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唇亡则齿寒,忻口失陷,太原就成了一座孤城,太原如果放弃,则整个华北的正面抗战等于宣告结束。
就在形势已危如累卵的时候,八路军却逆流而上。10月底,八路军总部率115师主力和129师769团由五台地区南下,进至正太路西端寿阳以南地区。
加上原已进入正太路的129师主力,八路军的主力已经摆在正太路两侧准备有所动作。
刚刚使日军第20师团尝尽苦头的129师又使沿正太路西犯的另一个日军师团——第109师团尝到了伏击的滋味。
当得到第109师团之第136联队的一个大队,由东冶头镇向昔阳进犯的消息时,他正对照着地图翻看着敌情通报。
他马上被这一条消息所吸引。当他的目光沿着日军前进路线看到黄崖底时,一个作战方案又形成了。
黄崖底地形复杂,小路从黄崖底经过时,正好处于两坡下的窄沟里,附近眼界开阔,便于隐蔽,是设伏的理想场所,特别是这里离大路很远,敌人又只有一个大队……
想到这里,定下了决心。他对参谋长李达交待完任务后,又补充道:“这一仗让771团担任主攻。”
771团自从被袭后,两次伏击都没参加,干部、战士都有点坐上了冷板凳的感觉,早就憋不住了。
一听到有战斗任务,还是担任主攻,那个兴奋劲就甭提了,都表示要打好这一仗,也让鬼子尝尝771团的铁拳头。
在战争中使作战力量得到正确的部署并不是件难事,难的是像这样将每一个可供调用兵力的作用发挥到极至。
这是一种艺术。不会用兵,八路军的几万部队不可能在敌后发展到几十万部队,更不会在抗战胜利后打败拥有800万军队的蒋介石。
除了会用兵,还要知兵、爱兵,做到官兵一致,才能够产生出无比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试想,军在抗战期间也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将领,不能说他们不会用兵,但为什么到了解放战争国共对阵时就不行了呢?恐怕不能知兵、爱兵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战斗就不用仔细描述了。当鬼子进入伏击圈后,所有埋伏在两侧山头上的轻重火器一齐开火,打得沟内的日军抱头鼠窜。
由于两侧山头通向沟底只有几条小路,部队不能对一团混乱的日军发起冲击,所以就只能以所有的火器向沟底齐射20分钟,然后安全、迅速地撤离战场。
事后,771团有的同志还觉得不过瘾,说:“要不是这个地形救了鬼子的命,我们就把鬼子全部收拾了。”
即使如此,黄崖底一战仍然取得了毙伤日军300余人,战马200余匹的重大胜利。
以后,一个日军随军记者用《过天险的黄崖底》为题,在东京的一份报纸上报道了日军在黄崖底遭受伏击的情况。
后来这份“歌颂”日军“勇敢战斗”的报纸被八路军缴获,一时成为八路军战士的笑谈。
从10月22日771团被日军偷袭起,至11月1日,指挥386旅在短短10天内接连打了3场伏击,歼灭日军逾千人。这与军十几万大军兵败娘子关形成了鲜明对比。
事实胜于雄辩,原来嘲讽的黄绍竑惨遭打脸,不得不承认:“打鬼子还是游击的法子好。”并主动找讨教游击战法。
- 慧博投研资讯-专业的出资研讨陈述大数据渠道-免费的研报共享渠道-慧博资讯2023-12-18
- 八月上旬必须重启矿山石材开采!河南罗山县召开矿山整治会议2023-12-18
- 视频资讯_逗游资讯中心2023-12-20